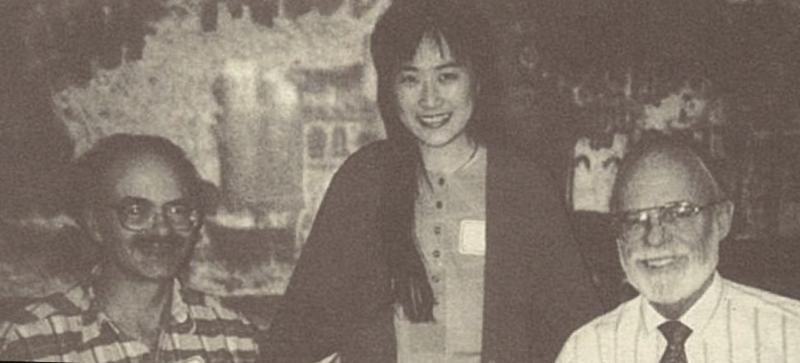
葉明理,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關懷生命協會理事。
文/ 汪盈利
投入動保運動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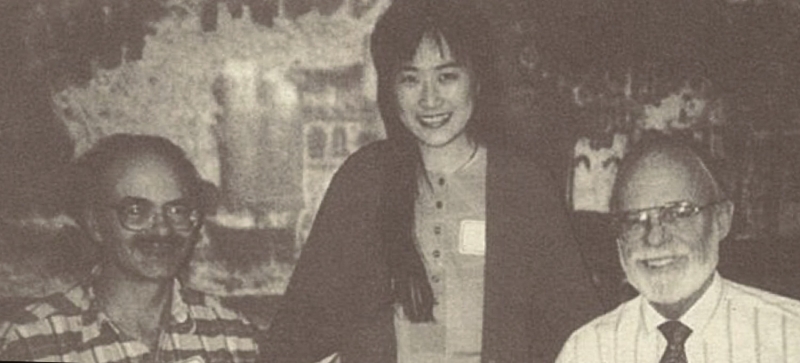 我這輩子到現在參與成立過四個團體,如果連動物園志工隊算在一起有五個:動物園解說志工、保護動物協會流浪動物之家、關懷生命協會,然後有狗醫生協會,我們現在另外再成立一個協會,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我這輩子到現在參與成立過四個團體,如果連動物園志工隊算在一起有五個:動物園解說志工、保護動物協會流浪動物之家、關懷生命協會,然後有狗醫生協會,我們現在另外再成立一個協會,動物輔助治療專業發展協會。
我是學護理的,在護理養成教育裡頭其實沒有動物這一塊,有的話大概也是實驗動物這種,就是將動物作為教材教具的,要不也是把動物視作為是公共衛生上的病媒、傳染媒介,所以老實講對動物的概念並不是友善的。身為護理人喜歡動物、想要幫助動物,但周圍沒有關心動物的朋友是很孤獨的,因此,當時心裡就有一個聲音:妳需要去找同伴。
社會運動的一個基礎其實是要有同伴的,大家相互取暖。我們那個禁止人民集會結社的年代根本沒有什麼動物團體,而我想找朋友呢,就只能翻電話簿,yellow page,找看看哪些地方會有喜歡動物的朋友。那個時候也只有動物園在招志工,就這樣子,去參加志工培訓,然後就真的認識很多都是比較喜歡動物的朋友,後來參與流浪動物之家的成立,再接著是關懷生命協會等等,在過程中和動保的接觸越來越深。
關懷與我
挫魚事件在記者發表會(1992 年)那時候我就去啦,是非常早的一批,我是創會連署三十名以內的創始會員之一,參加過協會成立大會。
我1993 年8 月出國,關懷1993 年年初成立沒多久我就出去了,就是因緣際會,剛好我申請的學校就在華府的附近,然後他們就叫我做駐美代表,所以我是外派單位,肩負重任,都不專心讀書,都在交朋友,哈哈!
我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去那邊交朋友,因為華府是首都,所有的動保組織大概在那裡都有一個headquarter(總部),所以我就寫信聯繫這些具影響力的動保團體,如PETA, ASPCA, Humanne Society 等。
所有團體都是我一個一個親自打電話去,我的說詞都是:「我是從台灣來的」然後人家就會說:「你們台灣真糟糕。」真的,那我說:「是,沒有錯,所以我們現在成立這樣一個團體(關懷生命協會),我們想要跟你學,不知道可不可以拜訪你。」
所以就好多團體,有一個list(名單),然後有空就去拜訪。那其實我在讀學位,只能用課餘的時間,在那裡做聯繫、協調。那段時間也幫協會收集很多美國他們動保法方面的資料,包括NGO 的組織結構、營運方式、議題的營造這些。
原先其實在大學的時候曾經考慮過說,我是不是應該要去改換跑道,去念獸醫、去念動物?我喜歡動物,當然要去念那個領域呀!可是現在回過頭來看,慢慢清楚一件事情:我學人的科學是對的、留在護理是對的,因為護理的訓練,幫助我能夠站在對方的立場想。因為若沒有社會科學的訓練,沒有助人專業的素養,很難站在對方的立場想事情,那就沒有辦法進入對方的世界,也就沒有那個縫隙可以去改變他。
另外,出國念書又幫關懷做這些駐美代表的事情,在跟這些動保團體聯繫的過程,也讓我釋懷了一件事情:在我們護理裡頭很強調的就是「caring」(關懷),白衣天使就是要有愛心對不對?但為什麼有愛心的護理人員,卻不被教導要愛護動物,反而是一種對動物不友善的養成教育?這是我在年輕時蠻介意的一個障礙,可是捫心自問,我就是喜歡這兩造,我喜歡人我也喜歡動物啊,所以我才會走進這樣跨這兩邊(護理與動保)的領域。
直到接觸國外的動保朋友,看到他們在動保組織裡頭也有護理人員的次團體,這點讓我釋懷了,證明了我的選擇是對的,也就是回歸到一個本質,就是你需要一個關懷的心,做動保和作護理都是一樣。
協會樹立的運動典範
我想關懷這十幾二十年,其實應該已經有一個工作模式的SOP 流程,算是一個動保社會運動的典型。關懷在1990 年代那段時間,其實是比較偏向所謂社會運動型態的團體,她不只是個動保團體喔,她是個社會運動的團體,就是像Peter Singer,在寫書的時候說他不養動物的,他不是愛動物起家的,但不養動物的人一樣可以幫助動物。
所以這也讓我看到了一點,你如果是社會運動理念經營型態的組織的話,就是要廣納百川,連那些不愛動物的人,如果你都可以讓他來跟你一起工作,這才成功,因為光用情感來做社會運動,是沒有辦法跟執政掌權者溝通的,社會運動就是為了要影響公共政策嘛,不然你幹嘛社會運動?
關懷是一個很棒的典範,因為我們那個時代的社會運動,大多屬於政治情結的社會運動,除了政治議題以外,比較具有典範的議題大概就是關懷。那個時候鯨豚啦、荒野那些,都還沒有出來。我知道有不少經過關懷的人,去到另外的這些組織,我想那時的關懷,應該多少對當時及現在其他非政治性的團體有相當影響,同時也培育了現今許多動保與環保團體的菁英。
這幾年參與動物保護運動的心得
其實想要參與社會運動,你一定得要讓自己浸淫這個議題裡,要有泡在這個議題裡面的過程,培養自己成為專家,因為沒有人比你更清楚你所關心的事情。我後來在美國完成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非營利性組織的菁英發展歷程,所以我讀蠻多NGO,NPO,third party 的東西,還有就是遊說,一些屬於社會運動的這些議題,我那個時候都有蠻多的涉入。
我真的覺得,誰能夠幫你代言?沒有人,只有你是唯一一個,就是讓自己成為專家。所有的政治人物,他們也都是你的代言者而已,當要做遊說工作時,其實你只是需要他的位階、他的角色,才能夠直接參與政治決策,所以你必須提供給他,要請他講話的那個材料。歸根結底,自己要準備好自己,成為那個代言者。所以啊,要影響公共政策,沒有別人了啦,就是你了!要嘛就不要做,要嘛就是要做到位。
我現在的感受是,其實這些拯救動物的事件,其實它的本相是在協助我們人類的成長,不需要那麼地在意它的成敗,我不是說不努力喔,而是說它其實提供一個道場,它在磨我們這些人,以這個為議題來學習人生當中應該學習的事情:包括面對事件的態度、學習處理問題的知識與技能、與人合作、解決問題,堅持與毅力、然後如何用當時合適的方式處理問題。它只是一個課題。而我自己在教育界也有受這樣的影響,就是,我學會不認定事情一定該怎麼做、或它該做成什麼樣子,或在哪個時間點該成就什麼事情,因為有太多影響的因素,但我堅持的是,一旦啟動面對問題的行動,就努力做到位,不求成敗,但求不遺憾。
也可以說我看透一件事情:動物福利沒有可以完全成就的一天,地獄不空誓不成佛?我們沒有那麼偉大啦。對我個人來講,成不成佛,沒有那麼重要,一階一階上,實際去改變比較重要。動物有苦難,人類何嘗沒有苦難?對不對。只是我們找到了這個領域,我們修這門課。
那重點是什麼呢?重點是這些後生晚輩,能夠從我們所做的事情當中學習,然後我們做過的事情,如果它具有價值,這些年輕人能夠傳承得下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