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年初,編輯部安排了「動物友善網」的記者李娉婷、關懷生命協會的「臺灣動物之聲」記者蔡育琳,與編輯龔玉玲和實習記者郭庭瑛,以信件、視訊和當面交流等方式談談對動保新聞與動保記者的想法。

其實,李娉婷與蔡育琳在動保新聞寫作上曾有教與學的連結。在關懷生命協會作為主辦單位之一的「臺灣動保青年論壇-2018寫手營」活動中,李娉婷以「前臺灣動物新聞網記者」的身分擔任了動保新聞寫作方面的講師,而蔡育琳則是主動報名參加寫手營的學員,當時她正為臺灣動物平權促進會工作。

距離寫手營已經過了一年半,如今李娉婷與蔡育琳在工作上也有了變化。在離開「臺灣動物新聞網」之後,李娉婷轉換跑道當了一年上班族,從事與動物保護無關的企劃。直到 2019 年年初她回到熟悉的動物新聞領域,加入了當時新成立的「動物友善網」,再度寫起新聞。而蔡育琳則是在寫手營中與關懷生命協會編輯龔玉玲重逢下,受邀為「臺灣動物之聲」網路論壇固定寫稿,而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新聞路線與報導風格。從關懷生命協會作為「臺灣動保青年論壇- 2018 寫手營」主辦者之一的立場而言,目前擔任協會動保記者的蔡育琳對協會而言不啻為舉辦寫手營的具體成果。

踏入新聞寫作的契機
李娉婷離開學校後的第一個工作就是進入中華民國保護動物協會的「臺灣動物新聞網」,在此之前其實很少寫東西(念工業設計的她都在做模型)。沒有動物新聞寫作的認識就入行,她說自己在做記者之前「真的都是一張白紙」。李娉婷在寫手營的「動保新聞現場」講座中曾自述:「我剛開始進新聞網的時候,其實真的什麼都不懂,一開始,做採訪一直遇到挫折,蠻常被呂幼綸主編責備。可是經過一段時間後,逐漸覺得在這個領域駕輕就熟起來,有議題出現時,我可以想到要怎麼做、怎麼寫、可以找到哪些資源,這是短短兩年半之內的轉變。」
相較之下,有些較資深的動保人是在已經熟悉動物議題之下,為了執行工作或是肩負傳媒任務,而去學寫新聞稿或成果報告,在人力資源有限的時候,甚至也要自己攝影拍照或編輯影片。在動保圈裡當了二十年貓狗志工與協會志工的蔡育琳便是一例。
蔡育琳有二十年的羅曼史小說寫作生涯,從1994 年出版第一本小說到 2014 年停筆之間,發表了 122 本作品。自覺碰到瓶頸,「愛情的賀爾蒙都用完了」,也就開始了新的寫作方向:「我曾經去上公民記者的課程,學習並製作影像,開始有一些採訪報導的機會,尤其是關於動保主題,因為是我長期關注的領域,更讓我想為此做點什麼。」本身就是動平會志工的她,除了幫忙寫文章,在2014年停筆後,做了幾年的動平會兼職工作,擔任臉書小編或是活動現場人員,後來才完全轉換到關懷生命協會的事務上。
「動物新聞」與「動保新聞」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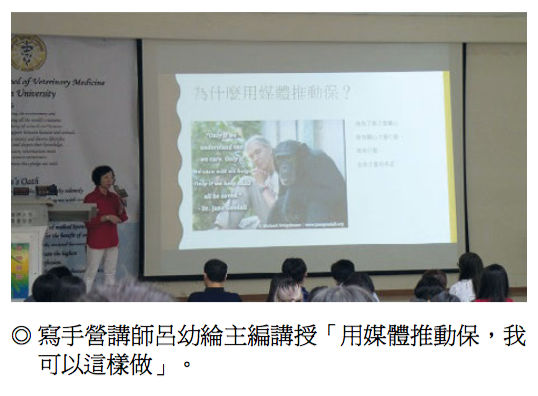
要了解「動物新聞」與「動保新聞」的差異,要先從「寵物新聞」談起。曾任「臺灣動物新聞網」主編,現於「動物友善網」任職的呂幼綸主編,在「2018 寫手營」的講座課「用媒體推動保,我可以這樣做」提到:「我大概是在民國 84 年開始在民生報主跑寵物新聞⋯⋯那個時候,據說我是第一個臺灣的寵物新聞記者,因為當時還沒有所謂的寵物新聞⋯⋯跑寵物新聞因為前無古人,所以自己去找採訪的對象,因為街上越來越多的寵物店、寵物飼料商,所以開始跑寵物店⋯⋯跑著跑著就跑歪了,覺得跑寵物新聞好沒有意思,那些東西寫一寫後,感覺好像沒有所謂的靈魂在裡面,所以我就開始報導半夜在馬路邊餵流浪貓狗的愛媽,跑去找到動物輔助治療的狗醫生協會⋯⋯」而如今網路常常可見的「寵物新聞」許多是來自網友分享的影音,偏好各種寵物的有趣情況,不是以動物保護為主要內容。
在主流媒體上,寵物題材以外的新聞可以籠統歸為「動物新聞」,而「動物新聞」跟「動保新聞」是有些差異的。李娉婷解釋說,「其實動物保護科的主管機關本身就是在農委會下面,一般的新聞媒體不會為了小小的領域特別做一個線,所以這一類全部都歸類在農業新聞線,並不會真的對動物保護的領域有所專精。」
一個最大的差別是在動物攻擊人類的報導角度,李娉婷補充說,一般媒體大部分仍會以人的角度撰寫,所以閱聽人在觀看這些新聞時,對動物產生的負面想法就會比較多。相對地,動保記者會避開對這些攻擊人類的動物以情緒性字眼來形容。李娉婷認為,除非真的有主流媒體能夠察覺到動保新聞這部分是有足夠的聲量效益值得他們投入,否則以過去的媒體編制來說,現今要發展出真正專屬於動保的新聞並不容易。
李娉婷也觀察到現在動保新聞增加不少,原因是近幾年主流媒體發現有越來越多的閱聽眾會開始關注動保議題,以及現今的動保團體行銷能力突飛猛進,除了有很多動保團體志工協助外,也能夠邀請到很多專業人員投入。在這種條件下,「動保新聞線」才有可能從「寵物新聞線」與「農業新聞線」獨立出來。
而呂幼綸主編在 2013 年底負責籌備「臺灣動物新聞網」時,就以「想要讓更多人理解動物保護」為目標,不侷限於「農業新聞線」下的動物新聞而已。鑑於「臺灣動物新聞網」的成果,龔玉玲認為 2014 年「臺灣動物新聞網」的開設,可以視為「動保新聞」邁向主流化的重要一步。此外,「2018 寫手營」也不妨記上一筆,它為動保圈較全面地展示了動物新聞寫作工作者的專業經驗,畢竟動保圈裡的專職記者似乎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職別。
誰是「動保記者」?
說到「動保記者」,蔡育琳說她的出發點不是想當記者,而是想要為動物做些事,只不過是採取了報導型態來向大眾介紹各種動物議題,對於報導內容只求確切而且平易近人,讓民眾願意閱讀並有所收穫。這個想法跟呂幼綸主編在寫手營曾傳達給學員的一樣,她請大家先不用糾結於「要具備研究背景才能寫出好報導」的想法上:「如果我們想做的只是突破同溫層,讓更多的人來認識、關心動保的話,我們寫的內容和方式,在層次上可能就不需要到朱淑娟老師所說的研究背景等等,大家可以先卸下心頭的重擔。」因此蔡育琳說:「我身為記者或動保記者如何被定義,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儘管如此,蔡育琳對於「動保記者」的定義還是有個建議,她覺得寬廣比狹窄好:「我常在關懷生命協會的網站找資料,看到深度好文就會暗自感嘆,怎麼這麼晚才讓我看到?這些作者包括學者專家、第一線志工、老師學生、關懷的同仁等等,我覺得他們也可以說是動保記者。」
蔡育琳在「臺灣動物之聲論壇」、「動保扎根教育平台」的文章,到目前為止有二、三十篇。一開始主要是寫編輯部企劃的內容,後來,較多她自己提出想跑的採訪或是主題,像是 Vegan街頭推廣、動物權遊行等,從比例上來說是偏向動物權/素食運動。龔玉玲覺得動保記者在臺灣已經是少數,其中跑動物權或素食運動新聞線的更是稀少,因此問她同不同意被設定為跑動物權/素食運動新聞線的記者,蔡育琳認為這不必嚴格劃分,但也不會義正辭嚴地排斥。蔡育琳一向認為這些用詞或是劃分界線都是人為的,跟動物本身無關,就以同伴動物、野生動物、經濟動物、實驗動物、展演動物為例:「當我第一次知道動物被分為這五類的時候,我心想這根本是人類如何使用動物的分類,對於被利用剝削的動物有什麼差別嗎?」
同樣地,蔡育琳覺得在關心動物的領域中有動保、野保、Vegan、動物權、動物福利等不同立場和行動,其中有交疊也有衝突之處。如果有人不想被分類,或是跨足多種類型,那也無所謂,重點應該是減少動物的痛苦、改善動物的處境。
蔡育琳說:「嚴格說起來,我只是一個業餘的記者,一個月只有 2、3 篇報導,卻已經是我的極限。自己唯一認識的專職動保記者就是李娉婷,她每天要產出 2、3 篇報導,隨身帶著筆電和相機,隨時要吸收整理訊息、趕進度編輯圖文,而我只能依照自己的步調慢慢做。」
不過,這對李娉婷來說也並非易事:「趕上時事與追消息本身就是工作內容之一,這對自身的身心靈是會造成傷害的。」在寫手營中她曾經具體說明這個狀況:「我一開始動保新聞的來源是設定 Google 快訊的關鍵字,當時我設定所有的動物,所以每天收到大量訊息轟炸,瀏覽這些訊息是一個非常累的工作,需要每天大量閱讀的能耐,我現在是沒有辦法像這樣子持續的。」李娉婷坦承經歷過一段資訊焦慮的時期,但已經好轉,進化為能夠消化這種焦慮的媒體人了。
動保新聞人的情緒勞動
蔡育琳提到在採訪過程中有時會對「受訪者太過熱心,提供太多訊息」,或是「有人提供新聞線索、資訊, 自己不能領會其新聞價值, 或是沒空、不想去採訪」的狀況感到困擾。李娉婷則認為直說無妨,不會拿「沒空」當理由:「評估之後覺得切入點不夠的話,跟對方說聲不好意思。」假如不方便去採訪但有新聞點的話,就詢問受訪者願不願意之後提供資料和照片,再電話訪問。
即使如此,蔡育琳還是覺得拒絕別人很難:「因為以後可能會請對方讓我採訪,所以考慮很多。」對於人際關係,李娉婷有其他層面的考慮,在寫手營的講座中她分享過:「當記者很容易跟受訪者成為朋友⋯但當了朋友之後,很多東西因為人情壓力不寫⋯⋯」如果動保記者跟一個團體或跟某位專家太熟悉,在新聞寫作過程中要拿捏跟對方的距離。
蔡育琳也想知道讀者若批評報導內容,對李娉婷會不會有所影響:「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通常我們都會參考這些建議,我們都能接受,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意見是滿重要的。」李娉婷還補充說:「但現在網友越來越多,有些批評與評論是沒有營養的,那個我們看看就好。」
關於動保記者的情緒勞動,龔玉玲分享呂幼綸主編在寫手營曾經講到的層面:「在寫動物新聞,或者在找關於動物的資料的時候,對我來講,我的心靈負擔是很沈重的」,因為大部分發出的稿子呈現了動物受虐的不幸結局,而她勉勵寫手營學員:「這個我覺得大家一定要想辦法能夠承受,也許我們是這個階段的工作者,也許是透過承受這些,我們才能慢慢的把動保引導到一個正確的方向,讓動物不要再遭受這些苦難。」
對此,蔡育琳也很有感觸,她分享去新北肉品市場採訪「為豬送行」活動以及動物權街頭推廣者的經驗:
那天非常冷還飄著雨,我騎車的時候都在發抖。一台台運豬的貨車從中南部出發,後車廂沒有任何遮蔽物,豬群一路受著風吹雨打,來到新北肉品市場被屠宰。我還沒看到豬,先聞到豬的氣味、聽到豬的哀號,雖然我沒有進入屠宰場看到血腥畫面,但一想到這是牠們臨死前的最後一段時間,確實受到很大震撼。原本我只計畫寫一篇報導〈臺灣首次為豬送行 臺北Animal Save〉,後來又多寫了一篇心得〈為動物送行,讓自己清醒〉,可以說是不得不寫,因為心中感觸太多。而〈真相與匿名-動物權推廣的多元時代〉這一篇算是比較有成就感的報導,因為被轉載到「關鍵評論」也引發注意,推廣活動主辦人 Jack 跟我說,在報導發表後,他們收到很多報名的訊息。這件事讓我覺得很開心,因為我沒有毅力走上街頭推廣,但經由報導的影響,能幫他們吸引一些夥伴,希望也能多少幫到動物。

如何突破同溫層
而「關鍵評論」的屬性並不像「臺灣動物新聞網」或關懷生命協會的網站擁有關心動物的主要讀者群,因此蔡育琳的文章刊登於「關鍵評論」後獲得的反應跟在動保圈場域內的大不相同,對此她並不在意:
我給自己設定的讀者本來就是社會大眾,他們可能不了解動保運動,我希望能引發他們的興趣和好奇,更進一步思考動保議題。「突破同溫層」是許多動保人期待的目標,因此我認為應該走向「動保大眾化」,首先要讓民眾願意看、看得懂,並提供一些做得到的建議,有了基礎再逐漸深化。
李娉婷覺得輕鬆、趣味新聞也能產生潛移默化的教育性,她在寫手營講座中跟學員分享過:
「ET Today 寵物雲」的粉絲數超高,大概有一千萬左右,報導調性是走輕鬆、比較詼諧、文青的這種,這些新聞比較容易讓民眾看,當然也會有不溫馨的,像是虐待動物這種,所以偶爾插入一些大議題的時候,被看到的機率也會比較高,畢竟有一千萬的粉絲,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還不錯的動物新聞推廣的方式。很多人就會覺得寵物雲就是可愛動物新聞,但其實他們每天要發五到七篇新聞,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因為我們以前在臺灣動物新聞網一天只要發兩篇,五到七篇就真的只能是網路抄、網路找。但是有大事件的時候,他們也會跟進,他們的傳播效果都會遠遠的比我們好非常多,他們會接觸到很多一般的民眾,所以我覺得可以不用抗拒投稿一般媒體,或是用這種比較輕鬆、詼諧的方式。
不過李娉婷本身並不會想寫逗趣的動物新聞,主要是因為已經有很多人在生產了:「這類的新聞也是有存在的必要性,只是以目前的我來說,比較不會去撰寫這方面的題材。」至於文字風格還是會受限於媒體的調性:「我一直以來就職的媒體都是以日報為主,每日固定必須要有兩篇中立客觀且不帶有記者情緒的新聞,故比較難看得出記者的文風,最多只能從文字架構上看出寫作習慣, 若是要看出個人的文章風格, 還是要在專欄、或是主題性的評論稿中才會比較明顯。」
而蔡育琳覺得建立個人風格的動保記者其實很多,這是由於她對於動保記者的定義比較寬廣,她覺得網路「自媒體」的經營者也是「動保記者」,像是 2019 年和夥伴合創「動保龍捲風」的龍緣之,以影片、圖文、採訪等方式,帶大家認識各國的動物議題與動保行動者。此外,許多動物權推廣者會自創IG、Youtube、FB粉專等等,這些網路自媒體都很有意義和影響力。特別像是「夠維根 Go Vegan 這個 Vegan 美食主題的自媒體,Youtube 訂閱數有 9 萬 6千(根據 2020 年 1 月底Youtube 的顯示數字),臉書粉絲將近有 9 萬,突破同溫層的成績有目共睹。
動保媒體人共同的目標
至於「自媒體」或網紅和職業動保記者的關係,會是競爭還是助力?蔡育琳請教李娉婷有什麼看法。李娉婷覺得大家做的題材很廣泛,目前看起來是各自發展,沒有交集:「以目前來說,不論是自媒體或是網紅,我認為都還不到競爭以及彼此幫助的程度,畢竟每個人的題材方面都還是不同,比較像是各自在開闢各自的領域,我們尚未找到一個能調適彼此的橋樑。」
而李娉婷也認為動保網紅或動保「自媒體」的出現是好的,能夠有機會讓每個人了解到各種與動物方面多元的議題,不再讓大眾侷限於動物新聞只有貓狗題材。蔡育琳也認為動保網紅或動保「自媒體」的出現乃是多多益善,因為「只要有心就可以成為記錄者、傳播者,每一個行動就可能是一個契機,引發人們對動物的關注與思考,進而讓這世界有改變的可能。」這也就是所有動保媒體人共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