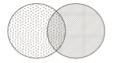
一、理想:使行政裁量衝突能夠調和
行政裁量之所以重要,乃因政府是透過行政,與公民產生最密切的接觸,而文官工作的日常,就是面對各方價值的衝突(如圖一),但設法在這些衝突當中,做出平衡的行政裁量(如圖二)。怎麼樣才能夠做出平衡的行政裁量呢?若是文官能夠「做該做的事」、「不做不該做的事」,不要去「做不該做的事」或「不做該做的事」,就能夠使文官的行政裁量恰如其分(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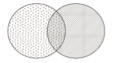

表一文官體系「行政裁量權」控制上的兩難
|
|
文官應不應該做 |
||
|
應該做 |
不應該做 |
||
|
文官的實際作為 |
行動 |
做了該做的 |
做不該做的事 |
|
不行動 |
不做該做的事 (型二錯誤) |
沒做不該做的 |
|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敦源(2002, 107)
二、現實:動保行政裁量的退縮日常
動物保護(以下稱動保)行政作為行政的一類,自然也會面臨許許多多價值衝突的困境,舉例來說,動保與公民財產權會產生衝突(飼主責任限縮其處置財產權)、動保與職業自由保障會產生衝突(限制巴特利雞籠的使用)、動保與學術自由保障產生衝突(動物實驗的禁止)、動保與信仰自由保障產生衝突(回教屠宰方式的禁止)(李建良,2004:6-10),而在我國動保行政日常中,幾乎只要是動保與其他價值產生衝突,動保行政裁量幾乎都會自我限縮,不必要的健康食品動物實驗、動物悶死車內、神豬飼養,都是這種案例[1],圖三就是目前動保裁量退縮的現況。

三、理論:動保行政裁量為何會退縮?
(一)道德政策造成行政裁量退縮的前因
動保政策屬於政策理論中很特殊的「道德政策」[2],一方面,因其具高度倫理價值,容易被立法機關制定出空有標準,卻缺乏行政資源予以執行的規範,因此文官在執法時常生無力感(Smith,1999; Sharp,2005),即圖三中的缺口,另方面,由於文官各自有其自身的價值,因此會透過行政裁量權來落實自己的想法,扭曲立法來執行自己的偏好(Meier,1994: 245),其狀態如圖四,此時,動保行政呈現的是偏移中線狀態,可能會自我限縮,但卻也有可能自我擴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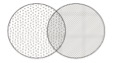
(二)監督機制造成行政裁量退縮的後果
動保行政必須面對來自立法機制的事前監督,與司法機制的事後監督[3]。
理論上,立法機制因此可以立法授權行政進行有益於動保的裁量,但實際上,因為立法機制通常會順從強勢利益團體的偏差動員(the mobolization of bias)(Schattschneider, 1960)而立法,除非公民受該立法侵害過度,而發出「警報」[4],否則侵害動物法益是一種常態,侵害的缺口如圖三,而立法的被動,常發生「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悲劇(陳敦源,2002:91),動保行政組織長年的弱勢、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禁止住戶飼養動物之規定、損害賠償請求權,不包含侵害動物生命,都是這種立法下的產物。
理論上,司法機制可以用來制衡,使侵害動保價值的行政不會發生,但實際上,司法機制受理行政爭議案件時,若遇動保法適用案件不足之處,只能夠透過自由心證進行裁判,在無更上位法律規範下,動保價值常在此時,屈居其他價值之下[5],這些判決透過事後的制衡,使得圖四動保行政的自我擴張不可能發生,只會自我限縮。
四、方法:如何修正動保行政裁量的退縮?
若希望修正動保行政裁量的退縮,別無他法,只能將動保價值明文訂入憲法,透過憲法中基本國策條款的「國家目標規定」性質來拘束整體國家機關(趙若竹,2020:21),包括行政機關,以及它的事前監督機制(立法機關)與事後制衡機制(司法機關)。
在立法機制方面,透過動保入憲,可以為動保行政添薪加火,行政機關可以「做該做的事」,主動編列足夠預算及人力(林明鏘,2016:3),立法機關必須予以支持,如此,便能夠如圖五,使動保行政裁量能往前進一步,有資源與意願與其他價值進行積極競合,不再自我退縮。
在司法機制方面,透過動保入憲,則「動物法益」與人民「財產權」、「學術自由」及「宗教(信仰)自由」保障之法益,彼此相互衝突時,則…司法權即得依憲法第23條之「比例原則」,衡量相關法益間之損害與利益大小,做成合憲性判斷(林明鏘,2016:3)。如此一來,便能夠如圖六,使侵害動物法益的機關「不做不該做的事」,進行必要的行政裁量退縮。
經過圖五、圖六的調整,其結果便能達成理想的裁量(圖二),也就是說,經過動保入憲法的調整,才有可能使得動保行政裁量能夠不在自我限縮,而能達成行政裁量的理想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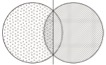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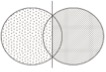
五、結論
我國過去便有過將道德政策透過入憲的策略,而矯正行政裁量退縮的經驗,在憲法條文第二次增修時,便曾將保障婦女、原住民、殘障同胞等道德價值,訂入基本國策,此後便使得我國在性別、原住民以及身障領域的行政,得到長足發展。此時,倡議動保入憲,並非將動保凌駕於人類之上,只是期待能夠使得未來動保行政裁量不再自我退縮,使動物獲得應有的福利。
參考資料
民視新聞網(200/7/27),〈僅有動物實驗不夠!衛福部健康食品標章受質疑〉,資料來源: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0727P06M1
李建良,2004,〈略論動物保護的憲法問題-憲法基本權的法裡思考〉,載於「多元價值、寬容與法律-亞圖‧考夫曼教授紀念集」。
林明鏘,2016,〈論動物保護法制之基本法制問題〉,《台灣動物法》,台北:新學林出版社。
陳敦源,2002,《民主與官僚》。台北:韋伯文化事業出版社。
農委會(2012/1/20),〈農委會呼籲兼顧宗教民俗意涵及動物福利停止神豬重量競賽〉。資料來源:https://www.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sub_theme=agri&id=4317。
傅玲靜,2020,〈從環境保護到動物保護--對於德國憲法的觀察〉,演講簡報。
趙若竹,2020,〈從動物虐待罪談動保入憲〉,《全國律師》,11月號。
Schattschneider,E.E.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Illinois: The Dryden Press: 20-46.
Sharp,E.B.2005. Morality Politics in American Citie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Smith,K.B.1999. “Clean Thoughts and Dirty Minds: The Politics of Porn.”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7(4):723-734.
McCubbins & Schawrtz.1984.“Congresstional Oversight Ovrlooked: Police Patrols versus Fire Alarm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cical Science 28:165-179.
Meier,K.J.1994. The Politics of Sin. New York:M.W.Sharpe.
[1]在實驗動物議題上,當健康食品進行沒有必要的動物實驗時,衛福部曾以「無論是食品或者是藥品,最後要運用到我們消費者的身上,一定要在有足夠科學的證據下,才能夠跟消費者說明。」為理由,進行動物實驗(民視新聞網,2020),在同伴動物關在炙熱的車子裏,警察主張狗本身是財務,與車窗同屬財產法益,跟人的生命、身體法益不一樣,致車內動物悶死」(趙若竹,2020:22),在經濟動物議題中,明顯違反動保法中「動物福利」規範的神豬飼養,農委會只能尊重「神豬作為祭祀酬神牲禮係國內民間信仰及常民文化」而不予處罰(農委會,2012)
[2]「道德政策」指的是--「至少有一個政策倡議聯盟,將該議題視為道德或罪惡,並且以道德訴求來倡議該政策」,在這些議題中,自認「道德」的一方,會將政策的另一方視為「罪惡政治」(the politics of sin),並「希望透過政府力量,將自身的價值觀強加到其他人身上」(Meier, 1994: 4-8)。
[3]行政裁量監督的相關概念請見傅玲靜(2020)。
[4]國會監督官僚因為成本的關係,通常都會選擇設立「警報器」(fire alarms)而非用「巡邏」(police patrols)的方式(McCubbins & Schawrtz, 1984: 165-179),防禦性的監督曠時費力成本太高,只能退而求其次。
[5]過去法院便曾否定對動保有益的行政裁量:動物保護法第27條第8款所保護者,既為人類生活安全衛生之社會法益,則就其「規範目的」以探求,不論原告所飼養貓隻之多寡,凡以同一特定場域飼養而經查獲其中有未為絕育者,核均適當認係以一個不作為而為該條款規範之違反,侵害社會法益數單一,應論以一行為;再參酌其未絕育貓隻之數量等一切違章情節予以加權,於法定5萬至25萬額度間為罰鍰裁處,始為適法。原處分按一貓一行為一罰,裁處原告155萬元罰鍰,乃有違法。